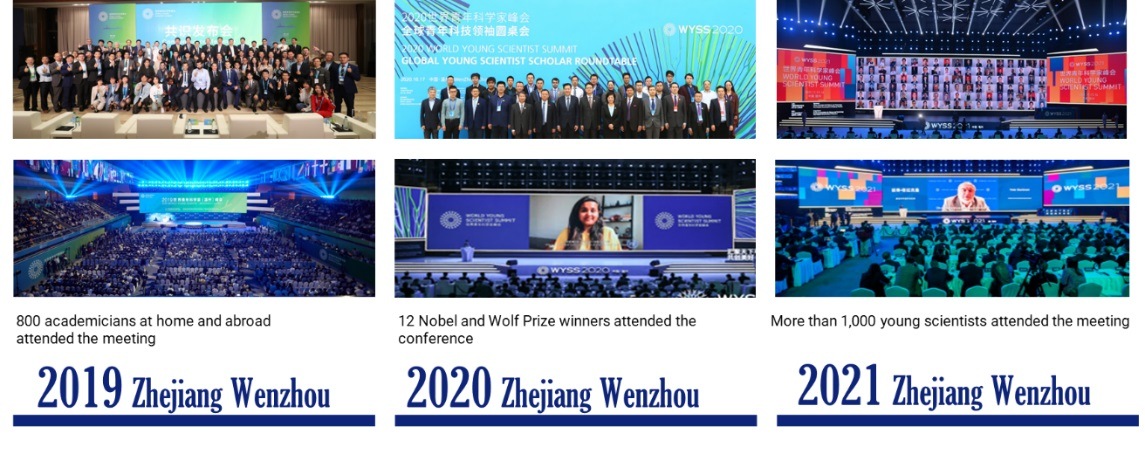民俗学者Aldina Camenisch和历史学者Mischa Marti简述在广州的生活

瑞士伯尔尼科尼茨Aldina Camenisch和Mischa Marti带着三个孩子举家迁往繁忙而充满活力的大都市广州,在那里生活了16个月——现在他们带着些许在中国的生活感触回到了科尼茨。

记者:Camenisch女士、Marti先生,你们从中国回来好几周了,有什么感受?
Mischa Marti:很好,谢谢!但是我也察觉到了您的话外之音,别人也经常这样话里有话地问我们:你们从中国回来了,高兴吗?问得好像我们之前生活在一个不毛之地似的。相反,我们在中国过得非常好。
记者:一说到中国,我们就想到“空气污染”、“难以忍受的工作节奏”和“政府监视”。
Aldina Camenisch:当然这些也都存在,但是西方社会所报道的中国形象确实是主观片面的。我们在中国的许多经历,一个普通西方人都不会跟他头脑中的中国联系起来。
记者:比如?
Camenisch:我们住在中国南部位于珠三角的广州市,那儿有2000万居民,坐火车到香港2小时,属于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聚集区。广州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中国城市,但同时洋溢着悠闲的热带风情且充满文化多样性。除了西方来的外国人,还有大量非洲黑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聚居区。真的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记者:那空气污染呢?
Martin:跟北京比起来还好。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绿色的街区,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公园,从我家阳台上一眼望去,能看到的唯有热带丛林和山上矗立的塔——生活质量极优!污染物超标的时候学校禁止学生在室外活动,这种情况在我们居住期间仅仅发生过三次。
记者:在一个中国居民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公寓位于中高产阶层聚居区,装有统一规格的栅栏。这样的小区并没有多奢侈,而是很正常的那种,反映了乡间邻里关系在大都市的传承和投射。我们要试着习惯那些一直非常友好的保安,四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其实没有他们,我们的安全感在中国任何地方也比在伯尔尼強。
记者:经济飞速增长对日常生活有何影响?
Camenisch:第一印象是巨多昂贵的小汽车在路上奔跑,瑞士都被比下去了。然后就是生活节奏和繁忙程度。在我们孩子去学校的路上有一栋新建高层居民楼。我们刚到时,还是一马平川,16个月后基本上就完工了。生生不息、持续变化、蓬勃活力、巨大规模,这些都让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
记者:特别是跟瑞士相比。
Camenisch:在瑞士我们总说“人口密度压力”,但自从我们从中国回来后,我感受最强烈的是:在我们许多城镇的街道上行人太少了。实际上现在我有时候还挺高兴能溶入到高峰时段公交车辆或伯尔尼火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
记者:中国人生活中真的只有工作吗?
Marti:一方面,中国人既不比我们懒惰,也不比我们勤奋——但是他们一旦全力以赴,就能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比我们达成更多目标。这种对于自我发展机会的意识我们经常察觉到。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相对受限,人们相对更需要依靠自身力量,这一点加大了工作压力,但同时也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记者:哪怕是中国人也是需要休息的。
Marti:当然。我的中国同事基本上和我操心的东西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脑袋中只有工作。在我教学的私立学校,很多中国老师希望能转到公立学校,因为在那里50岁就有可能提前退休了。
记者:太惬意了。
Marti:中国人对团队提出的新点子很快就能热情高涨,这一点我也印象深刻。他们不会首先顾虑重重、翻来覆去地讨论。还有中国式实用主义:一旦有问题出现,就去寻找解决方案。很酷!
Camenisch:许多积累了一定财产的中国人都会选择提前退休。在一些简单服务行业员工的上班时间一般显得很长,所以没有顾客的时候,你能看到他们有时候休息很久。事情都能更简单利索地着手进行。年轻企业家并不会花两年时间去钻研商业计划书,然后花一年时间去寻找机会。我从在中国的瑞士年轻企业家那里听说,许多事情能更快得到落实——进展也同样快,不管行不行得通。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发动机没那么强劲了。
Marti:中国怎样都没法让我们满意。当他们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威胁;中国经济减弱的时候,我们又都害怕(西方经济会受到牵连)。我的感觉是:许多中国人骄傲于他们的经济成就,但同时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灰色记忆尚存,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和政治存在再度快速冲突的可能性。
记者:他们可以自由谈论文化大革命吗?
Marti:我并不觉得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人们会因为害怕被监视而噤若寒蝉。实际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轻松翻越习俗和禁忌之墙。当然人们也知道存在网络管制,但有技术手段可以避开审查。
记者:您孩子们喜欢他们的私立学校吗?
Marti:非常喜欢。
记者:即使跟我们比起来,学习压力过于残酷,他们也喜欢吗?
Camenisch:跟我们这个富裕小国比起来中国竞争大多了。我们从我们较为熟悉的中国家庭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孩子作业很多,他们很晚或者周末都还在学习。
记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竞争有多大。
Camenisch:是的,特别是考大学的时候。只有经历大学教育才能有好的前途,职业教育才刚刚(重新)被重视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们在他们有限的业余时间里不能愉快地外出玩耍。
Marti:我班上有两三个女学生课后请了家教,她们还拉小提琴、做运动。玩的时间可能很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我从没感觉她们被奴役了,相反,她们成熟、幽默且对生活满意。
记者:西方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Camenisch:许多中国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很有了解,对瑞士也是——与之相反,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而言西方社会极其时髦,在中国的度假区我们看到了(几乎只有中国客人)的西式酒吧和咖啡店。消费态度有点让人惊异,在巨大的购物商城很多人可以度过整个周末。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批判过度拔高西方,要求复兴中国价值和传统。
记者:中国人遇到你们有什么反应?
Marti:我想用“正面种族主义”(Positive racism,此处意指白人因其他者身份获得特权和对本国人不公平的礼遇)来形容,我们经常享受优先权。有时候我们感觉跟明星一样,因为不停被拍照——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按照亚洲标准,他们有着大大的眼睛。每天在大街上、地铁里,到处有人给他们拍照。在城里还好,在乡下他们几乎成了外星人。幸亏孩子们一回瑞士就很快适应了该有的正常关注度。
Camenisch:当我现在见到在瑞士生活的亚洲人,我经常会想起中国人对我们的热情待客之道。好客的文化在我们这儿是如此陌生。但是外国人在中国永远是客,“融入”之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想要真正变成中国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Aldina Camenisch是民俗学者,她在巴塞尔大学从事主题为“在中国的瑞士人”的论文项目,这也是她去中国生活的原因。Mischa Marti是教师和历史学者,他在“éducation21”从事教学工作;在中国的时候,他在广州誉得莱国际学校教授德语。
伯尔尼报 记者:Jürg Steiner,译者:曾翌
摄影:Stefan Anderegg
原文地址:http://www.bernerzeitung.ch/region/bern/es-gab-situationen-da-fuehlten-wir-uns-wie-popstars/story/17441944